非常荣幸,受到虞院长的邀请,参加上海科技大学信息学院2024届的毕业典礼,和诸位青年科学家分享毕业的快乐,分享在特殊时刻免不了汹涌澎湃的人生感悟。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也曾梦想过要做一个科学家,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科技兴国,科学是客观的,代表进步的力量,科学家是万人景仰的职业。奈何我早在10岁懵懂未知的时就已经定下了人生走向。所以只能在之后的道路上,默默仰望曾经的梦想。今天能有机会见证诸位的人生进阶时刻,于我而言,也深感与有荣焉。
我假设大家在毕业的阶段,自我认定已经跨上了人生的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博士,可能很快就要转入职业生涯。最理想的人生,当然是一个一个台阶地往上走。你已经做好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因为你相信登顶之后会有“一览众山小”的风景在等待着你,你会拥有不同的视野,你有机会完成某种救赎人类的英雄梦想。
但你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就有所体会,时代并不算十分友好。事实上,眼下的情形很容易让人们回想起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似乎在每个新旧世纪的转折之际,开始时都会有一些好时光,让人看到例如经济增长,国际和平尤其是技术革命能够带来的美好生活。但很快随之而来的就是危机,战争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分裂的危机,在21世纪的时候,还叠加了未来人类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危机。我听过虞院长关于super eyes的演讲,我当时产生了两个很幼稚的问题,还没能有机会请教虞院长。第一个问题是,虞院长为我们提供的超过人类视觉的VR技术,能够让我们更加多维地看清自己吗?第二个问题是,更好的技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对象物,不仅看到正面,还能看到背面和侧面,然而,看得更清楚了之后,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更爱这个世界?
或许是注定的巧合,我最近在文学中也遇到了一个关于眼睛的故事。1975年,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离开捷克,去到法国的雷恩。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他曾经为他的妻子薇拉画过一幅画。画上是个男人,他掏出一只眼睛。为的是能够亲眼看到他平素从来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自己。从这幅画出发,《昆德拉传》的作者问的是:是谁在看谁?哪只眼睛通过另一只眼睛看见了自己?而我还想要说的是,当我们用失去一只眼睛的代价,用自身已经变得不完整的代价去和另一只眼睛对视,“看清楚”就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概念。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个最为深切的感受是,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并不是同一件事情,虽然它们的起点有可能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下产生的一个问题,而后者远比前者要复杂得多。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经常将有可能方向并不一致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或者说,假设两条前进的道路是同步的。我们很容易陶醉在科学的真理之中,因为相对单一的,可以抽象的理性更让人觉得安心,也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于是,往往在我们离登顶仅差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人类复杂性的山洪倾泻,我们的一路获得成了西西弗神话里的那块永远无法在山顶挺立哪怕是一秒的巨石。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说,20世纪初欧洲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否定理性的假说,相信偶然性,相信人类存在的局限性,相信“玫瑰花蕊、公里计数的界碑、人的手和爱、欲望或是万有引力定律具有同等重要性”,甚至科学都为这种对理性的否定提供了注脚,这些包括量子理论在内的假说却同样不能够阻挡人类被其自身的复杂性淹没的可能。事实上,科学进步和人类进步分裂成两条道路之时,人类的悲剧命运便被写入了程序。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科学家有所期待,期待科学家在帮助我们看到更清晰多维的世界和对象的同时,能够始终有一只“向内看”的眼睛,对自己和自己的同类抱有一种深沉的同情。唯有这种同情能够弥合两种道路的分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不让人类的复杂性成为遮蔽登顶时最后一级台阶的非理性力量,能够改写依然呈现悲剧性的人类命运的程序。因此,今天,在祝福各位顺利毕业的同时,愿已然是科学家的你们,能够在未来给我们带来科学的清明,帮助我们恢复对未来的信心。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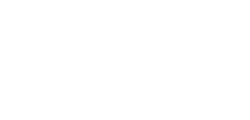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6855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6855号


